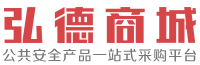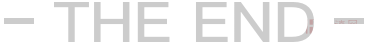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流变
业务专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新”,并不意味着“新近发明”,而是指“最近或者以新的形式被滥用”,事实上,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诞生至今已有数十年的时间。虽然在联合国框架之下的《国际禁毒公约》以及相关机构一直以来致力于构建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国际管制制度,然而在目前看来,新精神活性物质仍旧呈现出不断泛滥的趋势。不仅如此,在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各国颁布针对性的法律应对之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泛滥呈现出新的趋势,鉴于此,毒品管制策略还应当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种类流变
关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种类,联合国毒罪办将其分为合成大麻素、苯乙胺、合成卡西酮、色胺、植物类物质和苯二氮卓等几个大类,目前各国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防控也主要是根据以上分类来展开的。例如我国今年7月1日将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整类管制,对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概念就是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方式来进行的。然而目前来看,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本身缺乏外延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早已打破上述人为定义,蔓延到了其他的化学品领域。制造或发现这些物质的行为人,动机在于寻求脱离法律管制,同时达成流通或散布成瘾性物质,满足滥用需求的目的。从这个角度上看,目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经超越了“策划”的阶段,向更多元的路径发展。以往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大多是以某种物质作为“母体”,在此基础上进行策划形成的。最典型的如芬太尼类物质。我国于2019年5月1日将芬太尼类物质整类管制,将芬太尼母体的“基础结构”作为管制对象,从根本上消除了继续策划的可能性,因此芬太尼类物质的非法生产得到了极为有效的遏制。除此之外,域外立法常常采用的类似物管制、骨架管制等方法,以与母体的类似程度和母体的骨架结构作为评价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条件,这些策略对于策划类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都具有一定效果。然而,目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经摆脱了“母体”的限制,变得更加多元,行为人不断寻找更多种类的替代物,使得管制制度难以寻求管制的“基点”,例如更多的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出现,墨西哥鼠尾草、卡痛叶等等,都不是依据某一母体策划出来的,这就迫使当前的毒品管制制度重新回到“列举”的状态上去,对于已经创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手段造成了挑战。
危害变化
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变化的既往规律被打破,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的毒品泛滥,一般是需求推动供给的结果——吸毒群体对于毒品种类需求产生变化,毒品供给者予以响应,从而提供吸毒群体所需的毒品。这一供给链条一直以来都是毒品市场的普遍规律,例如苯丙胺类毒品大多由化学品直接合成,价格低廉,且其属于兴奋剂,容易被低龄群体所接受,此外,苯丙胺类毒品可以合成的属性也使其可摆脱毒源地的专属供给,将毒品供应行为分散化。在新精神活性物质出现之前,毒品的种类更迭大多维持了“需求牵引供给”的规律。然而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既有的规律,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药理属性和吸食后果是没有经过吸毒群体“验证”的,吸毒者并未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有任何消费意愿,但是供给者基于逃避法律的目的,寻找、策划或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并将其推向市场。此时吸毒者被动地接受了新精神活性物质。由于难以揣摩不断变化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用量,所以会造成大量的未知损害。例如一些国家近年来爆发的“处方药滥用危机”中,大量的疼痛患者在无法开具超出药用剂量的处方止疼药之后,会去寻求“街头毒品”,而这些毒品大多是未经验证毒理作用的,有些物质毒性极强,但生产者仅仅是为了逃避打击而予以制造,根本不在乎滥用者的安全,于是造成了大量的死亡案例。
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泛滥,以往主要采取修订立法、完善毒品管制制度以及争取及时响应不法分子的“策划”路线的办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行的做法。我国2015年颁行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是专门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规范性文件,在该办法中也建立了配套的专家论证、管制附表等措施,然而面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流变速率和滥用趋势,我们仍旧应当寻求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
一是继续完善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制度。我国当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制度,是以列举为基础的“临时管制”,在《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中,仍旧以列举作为基本的管制措施,同时设置了“先行管制,后续定位”的“非药用麻精药品”向“麻精药品”目录转化的措施,这类似于域外的临时管制,但其内核仍保持了传统的列举管制手段。2019年和2021年对于芬太尼和人工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整类管制,事实上是一种灵活的立法规则,且并不具有普适性。这对于目前已经产生种类变换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显然是不够的,域外的立法大多呈现出“组合拳”的状态,例如在列举的基础上,配合类似物管制、临时管制以及骨架管制,甚至还兼有早期预警系统。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我们也应当多管齐下,未雨绸缪。
二是修改与完善易制毒化学品立法。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加以遏制的重要手段,是通过前体管制掐断合成路径中的重要节点,而不是一一列举新精神活性物质本身。这一做法是域外常用的,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策划或者合成路径中,大多会存在比较明显的惯用的“节点物质”,这些物质的参与,可以使合成路径更为简单,或者使合成成本更为低廉,又或使合成环节更加安全,破坏这种“节点”,可以使行为人的成本上升、危险增大或者成本增高,迫使其放弃这一策划路径或者某一类物质的策划动机。我国对于毒品的管制极为严格,但是在易制毒化学品和相关物品的管理上还可以做一些提升。对于易制毒化学品管控,虽然制定了《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并进行了分类管理,但是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较少,一共3类仅23种,且有一定程度的漏洞,呈现出打击毒品严厉、打击易制毒化学品相对滞后的现象。修订和完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改变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滞后,有利于从根本上打消行为人寻求策划物质的动机,有效遏制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泛滥。
(作者马滔系湖南警察学院侦查系毒品犯罪侦查教研室主任、讲师;康午正、徐嘉华系湖南警察学院侦查系学生)
摘自中国禁毒报,侵删。